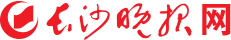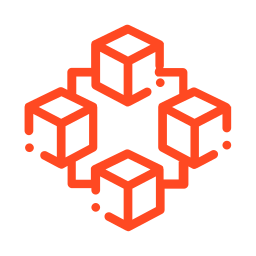亚坤夜读丨浪花里的光(有声)

我对海,总有一种投其怀抱的冲动。海阔天空,养育众生,无限湛蓝或白浪翻卷,一个无法揣摩的对象,永远在追风逐浪。当我深夜回到房间阳台上,眺望那一团玄墨色的海时,看海就变成了一个偃旗息鼓的动词,取而代之的是“听”。耳朵、心灵,以听的方式,从一个没有影像的动作,上演成一部连续播放的影片。从湖南长沙初来乍到海南昌江,就是从“听”迈出的第一步。
所有的听都是另一种看见。浪花是海的语言,海却从来都不会是安静的。昌江有海岸线60多公里,在绵亘的大海面前,每一段距离都是不可忽略的。固定在窗外的海岸线在夜晚变得黑沉,失重,但它必定是有颜色和光泽的。在这热带季风气候区,黏湿的空气被夜色洗涤干净,海水拍打岸的声音清晰入耳。海的一切回答都在岸边。海岸是最了解海的性格和情绪的,它在迎接拍打和波浪的涌动里书写着答案。再广阔的海也需要一道狭长的岸来停靠。海是流放者,一生都在寻找,流放者都在这里寻找自己的岸。
昌江更早之前称为昌化,境内流水就叫昌化江,自唐至清隶属儋州管辖。晚年苏轼的最后一个流放地就是儋州。这位流放者到昌江走的是一条自北向南的路线,行至此地,他被大海包围,在听海中度过那些不眠之夜。大海又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道路,每个人面对海,止步不前,却愈加激发生存的期待。也许正是这种期待,让人看见生命的安放与向往。过去的蛮荒之路,在今天已被网红打卡地所取代,但那时的长途跋涉意味的是无尽艰辛。一个人所走的路决定了他如何抵达人生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给他有过很多命名,我最喜欢“月夜徘徊者”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”这两个称谓。称谓里有张有弛,有动有静,有一往无前也有真实的犹豫和质疑。
海边的夜晚会因海水无限拉长,苏轼同样是一分一秒地度过。年过六旬的苏轼在儋州创办学堂,并言称“我本儋耳氏,寄生西蜀州”,引得不少跟随者不远千里追至此地。遇乡随俗,随遇而安,是他这位晚年仍遭流放者的真实命运。他目之所及,是亿万年来孤旷、狂寂,也沉静、优美的海,也是野力、追逐,也是柔绵、包容的海。也许面对大海,人生才会知道怎样走向一种开阔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颠沛的苏轼是深谙此道的,到了昌江,那些交集的悲欣随海风吹散,被浪花击碎成沙滩上的棋子石,以及野蛮生长的绿植丛林。大海的馈赠,他馈赠给了流离的生活。人总是在别处寻找自己,同行者高谈阔论苏轼在海南的豁达、快乐、知足,说他才是真正的乐天派,以疏朗心境创造流放地的文化,即使走到陆地的尽头,依然是躬耕自养、著书自娱,依然不影响他成为庶民的朋友。
在苏轼的履历上,海是生命的折返。沿着海岸线,他到过棋子湾附近的峻灵王庙,欣然题写了《峻灵王庙碑》。庙很小,藏在几棵高大的榕树下,木棉花落满周遭。保存至今的一块残碑之上,记载的是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五月,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谪于儋,“方壶蓬莱此别宫,峻灵独立秀且雄……我浮而西今复东,铭碑晔然照无穷。”有了此文,峻灵王庙就有了灵气和传承。可惜的是,当年“道路为家”的流放者,为自己建立海边的坐标,却在应召北还的归途中病逝。
任何消逝似乎都是宿命。半夜醒来,星光遁迹,黑暗与水,摇晃着此时的世界。旅途的疲惫让人若有恍惚,只身泅渡,海水从后面拥抱我,裹身向前。听海,很容易生发海水浮沉之感。人最渴盼的是不可抵达。海所制造的幻景,就是一种不可抵达。于是大海的一切被赋予了想象,浪漫、激情、欲望、搏斗、包容。真正的大海是通过我们的想象去抵达的。耀眼的珍珠也只是在蚌壳的体内发光。
听海,是在昌江上的一堂哲学课,这是真正接近并读懂昌江的唯一方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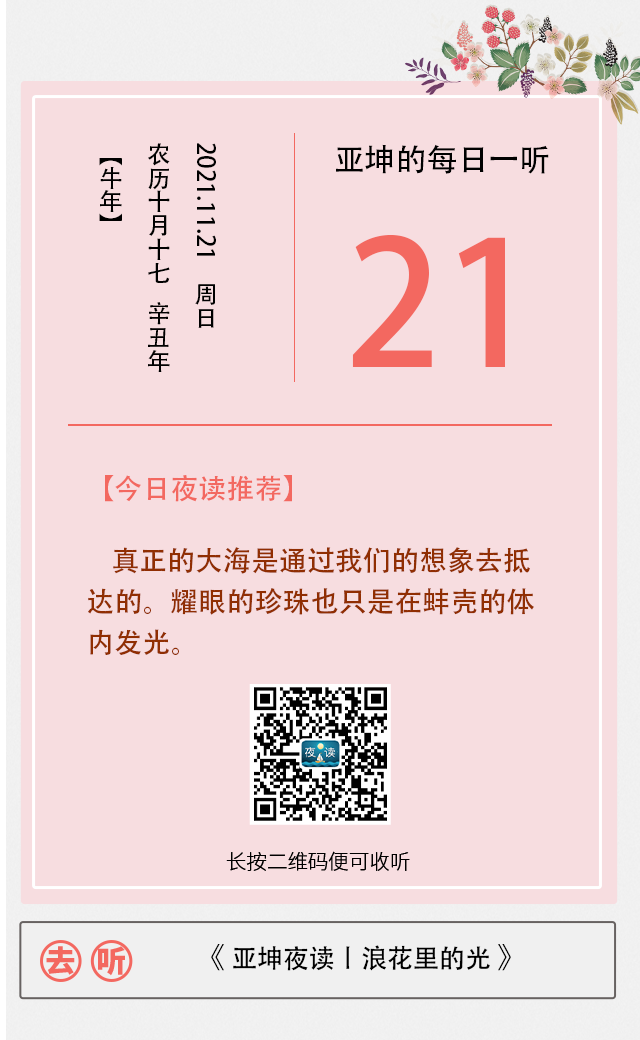
>>我要举报